丁淑贞 要感染就感染我吧
“给我一支蜡烛,那是青春跳动的火焰;给我一顶燕帽,那是守护生命的灿烂……”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是医护人员耳熟能详的旋律。每逢医院有文艺活动,都少不了这曲《天使之爱》。
亲笔创作《天使之爱》的正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丁淑贞。
回望30余年护理生涯,丁淑贞觉得自己有两件事干得很漂亮,创作《天使之爱》就是其中之一。当前由于护理人员少工作量大,不少护士难以排解自己的压力,对前途感到渺茫。丁淑贞感到,这个时候,护理界太需要鼓劲了,《天使之爱》就这样诞生了。电话那头,丁淑贞的语调略显激动,“一唱这首歌,浑身就有劲儿,可以相互鼓励,让大伙找到职业的归属感,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是一份崇高的事业。”
曾经是全院最年轻的护士长,护理过不计其数的病人,在同事眼中像“通了电的机器人”一样忙碌不休的丁淑贞其实是个老病号。罹患膀胱癌的她血尿已有5年,她总是吃点消炎药就扛过去了,直到尿流血块不止,一熬夜就呕吐时才去看病。因癌症复发她曾做过3次手术,至今仍然在化疗。成为病人后,丁淑贞更理解了患者的心情,对疾病的担忧,对手术的恐惧,患者的心理压力多大啊!她召开了一个畅谈会,让护士们讲讲自己当病人的体会。一位护士说:“我生病了住在自己工作的医院,环境相对熟悉,大夫、护士都是我的同事。可就是这样,上手术台前我的腿还是紧张得发抖。而普通患者呢,来了医院谁也不认识,肯定会格外不安。以前我们老说患者挑剔,现在我理解了,其实是他们心里紧张造成的。”这个畅谈会足足开了3个小时,护士们纷纷登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丁淑贞说:“我不喜欢苍白无力的说教,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换位思考,就会明白病人需要什么,我们能为病人做什么。”
丁淑贞也有遗憾。1985年她去日本研修护理,母亲突然辞逝,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业,父亲没有告诉她。一年后回国她才知道已经与母亲阴阳两隔,痛苦得揪心。她决心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弥补对母亲的愧疚。可是父亲病重期间,正赶上医院作为辽宁省卫生厅护理改革工作试点,众多工作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分身无术。在父亲临终的那个晚上,下半夜她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赶到父亲床前时,慈爱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了……从那以后,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手下的护士重复自己的遗憾,护士的父母生病了,丁淑贞就给她们放假。“我们一辈子都在照顾病人,如果父母生病不能亲自照顾,一旦发生意外,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SARS期间,她们这群与SARS病魔搏斗的战士竟然没有一张合影。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笔异常珍贵的人生财富。进SARS病房前,护士们紧张得脸通红。那时的她已经身患癌症,“要感染就感染我吧。”她第一个走进SARS病房,制定出一整套详细的预防措施,就连一张纸、一个处方的消毒和传递都有详细规定,还在全院示范“八步洗手法”,避免医护人员被感染。
记者让丁淑贞与同行分享她的护理管理经验,率直的她说,护理工作能不能做好,关键不在于护士,而要看头儿的思维导向,你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要先做到,行为示范的作用远远胜过上政治课。还有就是不要鹦鹉学舌,而是要尽快吃透领导的精神,结合自己的专业,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方案,便于下面的人执行。
电话那边传来她的阵阵咳嗽声,让人心疼。生病后的丁淑贞一直不愿离开岗位回家休养,对于病痛她很达观。“既然已经得病,单纯靠治疗是没有特效的,只要生命还在,就得提高生活质量,一旦闲下来,脑子就会生锈,成天想着我的病怎么样了。处于工作状态,一个病人接一个病人,忙得不可开交,就没有那么多脑细胞去胡思乱想了,为什么不过得轻松一些呢?” 陈海花 战地追梦人
第一次看到陈海花,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中。那时她刚刚从非洲利比里亚“维和”回来,虽然略显消瘦,但一身迷彩衬托出军人的刚毅。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总护士长办公室见到的陈海花,温柔、小巧,与身上的白色护士服相得益彰。提起南丁格尔奖章,她说这是自己一直向往的梦。
陈海花出生在青海省西宁市,1984年入伍后先在护校学习,后一直在城市的大医院工作,而她的心里还藏着一个军人情结。
2006年3月,当陈海花得知医院正在筹组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队的时候,正在上海出差的她立即给院领导打电话,坚决请战。而这时她的孩子只有8岁,丈夫在该院的肝胆外科任副主任,工作非常繁忙。然而丈夫的支持和她的坚决消除了院领导的顾虑,任命她为维和医疗队护士长。
“作为一名和平年代的军人,很少有机会经历战争,自己挺幸运的。”当听说护士长没有后备人选的时候,她还是着实紧张了一阵。作为护士中年龄偏大的队员,咬牙挺过了一个月的集训,她和队友们上路了。
利比里亚的贫穷超出了想象,基础建设很差,基本的卫生保障根本没有。更可怕的是,他们接触的患者HIV阳性携带率高达72%,40%的HIV阳性患者合并开放性肺结核。
陈海花和7名护士被分配到绥德鲁唯一一家二级医院,来不及适应当地的环境,陈海花就承担了接诊的工作。由于病人大部分患有严重的传染病,护士们穿刺、抽血、处理呕吐和分泌物都具有高风险。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陈海花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对护士们说:“我是护士长,我的护理经验比你们丰富,基础技术比你们扎实,由我先上,才能确保安全。”
他们接诊的第一名病人,是位艾滋病伴开放性结核并感染了恶性疟疾的埃塞俄比亚维和士兵。陈海花穿上防护服、戴上胶皮手套和口罩,从容地走进病房,在医生的指导下严密监测病人生命体征,做好各项急救准备。在给患者输液时,这名黑人士兵躁动不安,无法进行正常的操作。陈海花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技术,一次性完成了高风险、高难度的操作。完成治疗后,她又小心翼翼地处理好患者污染的床单被子,倾倒消毒排泄物,帮助患者擦洗玷污的皮肤……当她走出病房时,衣服已全部湿透了。8个月中他们先后救护HIV阳性患者1000余名,疟疾患者186名,转运后送重症患者68名。
陈海花和护士们还将服务充实到了每一个细节。他们针对病人所在的国度、民族、宗教信仰和病情需要,合理调剂膳食。埃塞俄比亚病员多数只会讲母语,他们就专门印制了英埃语对照的《住院须知》和伙食保障清单。在病房内设立了便利食品柜,摆放牛奶、饼干、果汁等食品,让病人随时取用。医疗队员生活物资全部由联合国供给,他们常常把全队仅有的蔬菜留给患者。
陈海花凭着过硬的护理技术,在简陋的病房里,完成了好几个第一:第一次接诊艾滋病人、第一次转诊危重病人、第一次护理疟疾患者、第一次护理登革热患者、第一次为产妇接生……每完成一次护理,她都要把自己的经验体会记录下来,告诉大家注意事项:给病人做静脉穿刺时,不要急于下针,一定要把血管找准,做到“一针见血”;病人怕痛,打针时一定要想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消除紧张心理;患者的排泄物是可怕的传染源,一定要及时清理干净,千万不要沾到身上……在她的细心指导下,护士们的护理技术迅速提高,救治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感染。
虽然陈海花从进入护校的第一天就知道了南丁格尔和南丁格尔奖章,但是她从来不敢往那上面想。“一直以来,我的目标是尽力做好自己该做、能做的事。”陈海花没有想到,从重庆大坪医院到北京军区总医院,20多年护理工作中所做的点点滴滴,大家都看在眼里,南丁格尔奖就这样离她越来越近。
现在的她,觉得奖章变成了一条小鞭子,让她没有了退路。 罗少霞 特别行政区的“特别护士”
38年的护理历程,上千次往返于内地与澳门之间,不计其数的大小奖项,多个社会慈善团体的倡导者……所有的量词都盖不过一次南丁格尔奖带给她的成就。她就是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澳门镜湖医院护理部主任罗少霞。自1983年以来,澳门第一次参与祖国南丁格尔奖的评选,罗少霞是澳门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今年57岁的罗少霞得知自己获得了南丁格尔奖,很谦虚地说:“澳门参与评选是很荣幸的事,这次光荣不是我自己的,护士工作是群体性工作,所以这个荣誉应该是集体的。”
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本身有其特殊性。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护理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澳门发挥自身的优势,不仅汲取大陆的护理文化,也融会贯通了香港及国外的护理经验。“身为护理人员要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虽然我们面对着不少困难及艰苦,但仍应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我希望可以引进各地先进的护理理念、科学理论、技术和实践经验,丰富护理工作的内涵,以满足21世纪社会人群对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罗少霞作为澳门护士学会的会长,热衷于澳门和各地的业务交流。
罗少霞小时候也生病住过医院,小时候她对护士就有一种羡慕欣赏的感觉。罗少霞自1969年从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毕业后就进入镜湖医院从事护理工作,选择护理专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她有着13年妇产科护士的工作历程、13年外科护士的工作经验、12年护理部主任的管理经验。
怎样当好护士,怎样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是罗少霞一直在考虑的事。她经常被患者看病的一些细节打动,例如倾家荡产挽救至爱的生命,老两口搀扶相伴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等。“作为一名护士,应该是患者的至亲,因为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是你陪伴在他们的左右。”“病人的心理是很微妙的,生病带来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心也生病了,生理上的病痛还是小事,心理上的折磨才叫难受。”
一次,外科病房住进一位鼻咽癌晚期女患者,生命即将结束,患者的一切行为、表情都是漠然的,只是躺在床上等死。细心的罗少霞发现总是这个患者的妈妈在照顾她,难道她没有别的亲人,没有丈夫孩子?任凭护士怎样跟她交流,她都是不理不睬。后来罗少霞开始做患者妈妈的工作,问她一些患者的情况,慢慢地了解到,这位患者的丈夫抛弃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只剩下孤单的她,找不到丈夫,也变得一无所有。“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无可奈何,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无可奈何。这个病人的眼神里就是这种表情。”后来在罗少霞的帮助下,患者的丈夫找到了。当丈夫带着两个女儿来到病房的时候,这名女患者不停地流泪,感谢护士。这个场景深深打动了罗少霞,从此她决定从事临终关怀工作,让每位病人的最后一刻都能圆满、心安。
罗少霞还有3年就该退休了。“退休之后我也不会闲着,我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要做。”罗少霞不仅热衷于护理工作,还参与了癌症患者爱心之友协进会工作,帮助癌症患者筹募资金,开展活动。“让每一个人都帮助身边的癌症患者,他们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除此之外,罗少霞还参与澳门临终关怀医院的护理工作,为垂死边缘的人提供贴心的服务。罗少霞说:“《南丁格尔礼赞》中,朗费罗这样写道:‘那盏小小的油灯,射出了划时代的光芒’。而我希望在祖国内地与澳门之间,搭建起合作的桥梁。我愿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护理事业。” 泽仁娜姆 用爱托起人间天堂
虽然对于麻风病的知识并不陌生,但直到1994年10月调到青海省同仁慢性病防治院工作,泽仁娜姆才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第一眼看到那些容貌严重损坏的麻风病人,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惊恐。这时,一位老奶奶正好走过来,她和我对视了一眼,便低下头走开了。
我想,一定是我脸上惊恐的表情让她受到了伤害。”
13年过去了,在与麻风病人的朝夕相处中,泽仁娜姆心中的惊恐渐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关爱和体谅。有一次,一家电视台到防治院来拍摄一部专题片,其中一个镜头设计是泽仁娜姆为患者梳头。拍摄完成后,患者扭过头来对泽仁娜姆说,姑娘,你给我梳完头后回去一定要洗手,千万要洗干净。“那是一位现症患者,也就意味着她可能传染别人。因为我给她梳头时没戴手套,患者担心我因为接触她的汗液而被传染上,一再叮嘱我回去把手洗干净。”泽仁娜姆说:“麻风病人虽然面容受损,但他们同样有着善良的心。”
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得麻风病人的治疗存在一定难度,不少患者都有足部溃烂的症状,久治不愈。为了帮助患者更快地康复,泽仁娜姆动起了脑筋:“我们这里阳光充足、紫外线强,能不能装一台太阳能热水器,让患者可以有热水泡泡脚,好得更快些?”在她的建议下,医院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麻风病人在闲暇时,可以坐在院子里用热水泡脚。
作为主管护师的泽仁娜姆深知,对于30多位因为残老留院的麻风病患者而言,防治院是他们唯一的容身之地。她除了每天为麻风病人打针、发药、换药之外,还把患者生活上的疾苦放在心上。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泽仁娜姆发现藏族老奶奶桑杰措生活十分拮据,她就和同事一起把老人作为自己的帮扶对象,经常给老人送去面粉、青油和生活用品。闲聊时,泽仁娜姆得知老人过冬只有一条裤子。回家后,她就让丈夫骑着摩托车带着自己到17公里之外的州府所在地给老人买来合身的衣物。
为了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线索调查以及出院病人的跟踪随访工作,泽仁娜姆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方圆几百公里有麻风病人的县乡都留下了她的足迹。2006年6月,为了调查出院患者的存活情况,泽仁娜姆和两位同事一起前往位于大山顶部的双处村。当时恰逢雨季,山路被雨水冲毁,无法通行。泽仁娜姆和同事们返回山下,借来铁锹,重新上山,一边走一边修路,终于在下午登上了山顶,找到了两位已经出院的麻风病患者。其中一位是70多岁的仁青加老大爷,老人因为白内障已经双目失明。“我们找到他时,看到老人穿着一条黄裤子,上面打着蓝布补丁,衣服上有好几个大窟窿,左脚穿着一只破球鞋,右脚穿着一只手编的草拖鞋。因为山路被冲坏了,老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东西吃了。”
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麻风病人存在恐惧、歧视和排斥心理,在藏族的传统观念中,麻风病也一直被视为不治之症,麻风病患者往往被驱逐、隔离。麻风病患者出院后无人照顾的困窘境况,泽仁娜姆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麻风病人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但生活却如此不同,我心里真是太不好受了。”泽仁娜姆向院领导提出残疾病人应列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范围,尤其是无人照顾的孤寡出院病人应接到防治院来生活的建议。在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如今防治院的病人都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今年,治愈出院的孤寡老人也很快能拿到最低生活保障了。”电话那头,泽仁娜姆的声音里透着激动和喜悦。
泽仁娜姆的名字是她的爷爷给起的。在藏语里,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永远的天使”。在残老留院的麻风病患者心中,在无人照顾的孤寡出院患者心中,青海省同仁慢性病防治院就是他们的天堂,而泽仁娜姆和她的同事们就是带给他们希望的天使。 聂淑娟 天使学者情洒边疆
今年刚满60岁的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护理部主任聂淑娟,在回顾40多年的护理生涯时说,最难忘的要属1986年。当时,和田地区洛浦县暴发传染性肝炎,引起一片恐慌,政府要求各大医院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一线抢救。由于洛浦县偏远落后、疫情严重,当地百姓和牲畜,以及去支援的医护人员都要同喝一个地沟里的蓄水,报名时大家都有所顾虑。
聂淑娟心想,在护理管理人员中,自己算年轻的,应该先去报名。身为护理部主任的聂淑娟第一个报名之后,大家开始抢着报名,一支迅速组建起来的救助队很快到达了疫区。
由于当地条件恶劣,病人们全都挤在狭小的乡卫生院病房里,睡在地上简陋的床板上。聂淑娟和另外两名护士尽可能地做到消毒隔离、改善病房环境、做好清洁卫生。即使是在护理传染性极强的病人时,她们也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给病人喂水、喂饭、擦身、更衣。由于输液架不够,她们就在土墙上打了一排排木桩当架子,打针时只能跪着操作。由于人手不足,聂淑娟等3名护理人员要照顾上百名病人,24小时连轴转。没几天,她们的眼睛熬红了、嗓音嘶哑了、嘴唇肿起了水泡,人也消瘦了一大圈。当时大家都太忙了,根本没有注意到给医护人员做饭的大师傅,整张脸都变黄了,他也被传染了!
回到乌鲁木齐后,聂淑娟她们接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保肝治疗。怕吗?聂淑娟说,洛浦县是贫困县,鸡蛋和白糖都是国家特拨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手里拿着鸡蛋,一路追着我们乘坐的汽车。我们护理过的一位肝昏迷孕妇苏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白衣圣人亚克西”。“说真的,只要一看到病人、一忙起来,所有的担心就都没了,什么都忘了。”这一段经历让聂淑娟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职业虽然平凡但很有价值!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聂淑娟所在医院的规模也在扩大,新的部门和科室应运而生。聂淑娟参加了ICU病房、CCU病房、肾移植室、骨髓移植室、心血管专科医院、骨科医院、肝病中心等的筹建工作,每一个科室的成立都凝聚了她的全部心血。在医院各项新开展的、复杂的大手术特级护理方面,她率领护士们制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护理方案,为这些高难度手术的成功实施作出了贡献。2003年春天SARS肆虐时,聂淑娟不顾身体有病,依然投入到建立发热门诊的工作中。她率领各科护士长,凭着丰富的护理经验对门诊格局进行科学设计,从墙体打通到封堵,从物品摆放到隔离工具的落实,每一项工作她都要亲自上阵,常常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
如今,已经从护理一线退下来的聂淑娟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护理教育和在职培训中。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相对不便,基层的护理人员带职培训的机会很少。以聂淑娟为首的新疆护理学会就把培训班办到地州去,一个会场不够,还要多加几个分会场,让学员们通过电视观摩学习。她经常赶赴最边远的山区,把护理新知传播给最基层的医护人员。
每次培训应得的收入,聂淑娟一分钱也没有收过。她说:“基层医护人员的求知欲望特别强烈,也都特别希望我们去讲课。他们告诉我,自从听了课,对把护理工作干好充满信心!”
作为医院唯一的护理学副教授和学科带头人,聂淑娟还肩负着高层次护理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教学中,她将多年的护理临床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
无论是给本科的护理学生还是基层的护理学员讲课,聂淑娟总是告诉他们:我们选择了护士这份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护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发展还比较滞后,护理工作要发展,就必须走一条专科之路。护士不仅是天使,更应该是学者! 《健康报》2007.07.18 8版 编辑:李玉花
作者:张灿灿 孔令敏 谭嘉 薛原 闫�� 王燕松 赵瑞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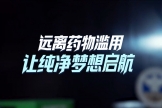
2025年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025年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互联网医院全面升级!足不出户“坐享”全流程优质诊疗
互联网医院全面升级!足不出户“坐享”全流程优质诊疗